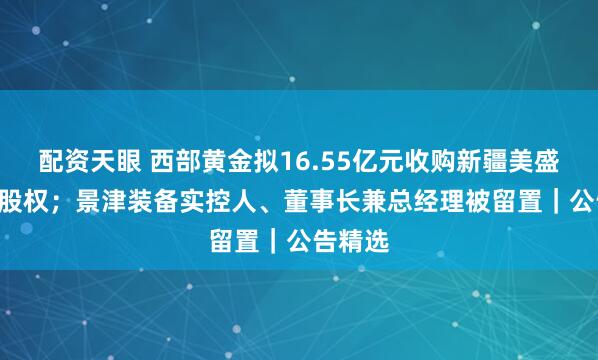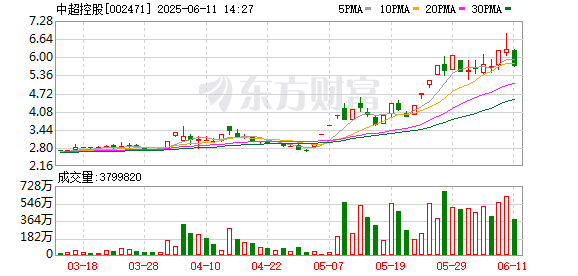“1955年2月初安全的股票配资平台,毛主席让我给你带句话——‘别往回想,好好治病,咱们都得向前看。’”医护人员推门而入时轻声说。病床上的凯丰勉强点头,嘴角掠过一丝感激。
这一声问候,在屋里回荡了很久。谁都明白,眼前的病人不仅是中宣部副部长,更是昔年在遵义会上顶撞过毛主席的那个人。近二十年的风云翻卷,使二人从激烈争论到惺惺相惜,世事的跌宕大概就藏在这简单一句“向前看”里。

凯丰原名何克全,1915年生于安徽休宁,少年时就“刀笔双绝”。红军时期,组织看中他的笔杆子,把他调往总供给部。倘若没有长征,这个“写稿子的人”或许不会卷入最前线的路线之争,但命运往往爱开玩笑——1935年1月,遵义会议召开,他站在了博古一边。
那次会议气氛紧绷。凯丰拍着桌子反问:“凭《孙子兵法》也能打仗?”一句话把主席逼得停顿片刻。会后,他的职务被暂时免去。失意的夜晚,聂荣臻送来一碗面,顺口劝道:“再犟下去,部队可就走不动了。”这一句,像冷水浇头。凯丰反复琢磨自己到底错在何处,终于写下自我批评长信交给张闻天。信里只有八个字最醒目:路线错了,唯有补课。
红军过雪山草地时,凯丰跟在宣传队后面沿途采访。他把士兵脚上的冻疮、老百姓送水的瓢,细细写进简报。毛主席翻到其中一段,批注:“笔墨靠近士气,此人可救。”不久,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会议恢复了他的工作。他没想到,恢复职务的第一项任务竟是主持批判恶霸大会,而提议者正是毛主席。自那以后,他常说“跟毛主席干工作,有股子信任感压着人,马虎不得”。

进入全面抗战时期,凯丰被派到延安,协助整顿《解放日报》。王明在会上散布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的口号,他拍案而起:“救亡靠自立,不能等洋人开药方。”尖锐得让人捏把汗。毛主席会后当众握他的手,说:“言辞利,但心更利。”这一次,他彻底站到了正确一边。
延安整风期间,凯丰把“知错能改”四字写在黑板上,自嘲当年“冲动加书生气”。毛主席偶尔来听汇报,提起往事只是摆摆手:“这段都过去了,重要的是你现在在哪边。”两人从此私下往来。凯丰爱写剧本,请毛主席评点,主席偶尔也“挑刺”,把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写在扉页寄回。凯丰看完哈哈大笑,转身就把稿子撕掉重来。
1945年七大推举中央委员,他因为曾经顶撞过主席,票数略显尴尬。毛主席三次在会上说“凯丰同志是好同志”,最终仍落选。散会那晚,主席走进他宿舍,递上一支半截香烟,轻声道:“别闷,革命靠干,不靠名堂。”烟雾袅袅,两人沉默良久,窗外延河水声更急。

抗战胜利后,凯丰赶赴东北组建《东北日报》。纸张紧缺,他干脆让排字工人把旧报纸拆开当底板,一版又一版冒着墨香送到连队。报纸第一次刊出时,上方四个遒劲大字“东北日报”正是毛主席亲笔。拿着报头他兴奋得像个孩子,连夜写信:“主席字如号角,边读边想起在长征路上您背着草鞋写口号的事。”回信只寥寥几句:报纸办得不错,可别忘了休息。
建国后,中宣部忙得天昏地暗,凯丰常常通宵校样。会议间隙,他咳得胸膛疼,满不在乎地说“老毛病”。清查身体时,医院在肺部发现阴影,他仍拖着病体参加中央会议。直到1955年1月,确诊为癌症无法再瞒。组织安排住院,繁忙的文件改由秘书送批。毛主席批阅后,特地在纸角写下:“望克全同志安心治疗,一切事有组织负责。”
可病情比想象凶险。二月初那天,毛主席托身边工作人员带去那句“向前看”。凯丰把字条放在枕边反复端详。后来他对护士说自己最怕拖累工作,怕的是报纸上缺失那股子锐气。护士悄悄告诉他:“主席让我们叮嘱你,笔可以歇一歇,命不能歇。”

三月下旬,病房的灯光渐暗,凯丰在清醒时最后一次提笔,想给毛主席写信。纸上只写成两行:“主席,您说过要我向前看。可我这回,恐怕真要止步了。”话未完,人已力竭。工作人员把未写完的信和那张“向前看”的字条一起装入档案。49岁的生命定格,笔杆却像插在历史上的一枚书签,提醒后来者:错了不可怕,怕的是不改;跌倒不可怕,怕的是不再向前。
如今回望,凯丰的故事未必轰轰烈烈,却道出革命队伍中最常见也最可贵的一幕:知错、改错,再以全部热忱投入正确的道路。那张薄薄的字条,从1955年一直传到今天,像一盏并不耀眼却持久闪烁的小灯,照着向前的路。
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助手网 国民党代理排长带22人投奔红军,征战16年升半级,授衔愁坏罗荣桓
- 下一篇:没有了